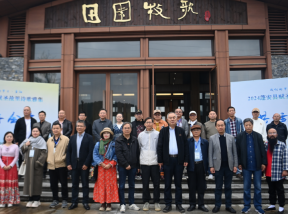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河北毕俊厚 于 2018-8-20 16:44 编辑
大雾中(组诗) 文/河北·毕俊厚
乡下的麻雀
在乡下,那么多的麻雀,它们灰灰的 盘旋在村子四周,觅食吃。
有时,它们也三三两两,掠过庄稼地 谨小慎微地到村子里,农户的园子偷食。 更多时候,它们是成群结队。旁若无人地 在稻谷堆,大肆抢劫。
有一次,大雪封门,山里、农田一片素白 整队整队的麻雀,像溃不成军的日本鬼子,冲进村里。 猪圈、鸡栏、牛舍、马厩,一片片阵地沦陷
我在目睹场景的时候,仿佛看到断荒期,小脚的母亲们 她们泪眼巴巴,接受着饥饿。为了腹中的孩子 她们疯狂地掠夺着赖以生存的食物
泸州的长江
长江流经到泸州,气息是均匀的。 平铺直叙的江面,偶尔有几朵小浪花 也有缎面似的皱纹。
江面上,小船不多,大船也不多。 只有岸边,堆积着光滑的石头 像是一个个刚刚跳出生活的人 棱角全无。
在我的想象中,长江是咆哮的 像是醉酒之人。而此刻 安静的长江,步态优雅地流淌着 毫无疲倦之意。
长江边那些捡石子的人 他们,也无疲倦之意。一定是喝了泸州老窖的缘故 是的。他们一定是被酒神相缠 忘记回家的一群人
只有一刻,列车是存在的
一整夜,我都在列车中度过 一整夜,“哐当”声,淹没了来时的路径 一整夜,呼啸的风声中,我 惴惴不安地,看到一颗陨落的星光
只是那一刻,列车是存在的 而滑落的,却是越来越远的,故乡的 风景和丢失已久的人
一架算盘
也许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更多的年头了。尘土下 它悄无声息地 忍受着 孤独和寂寥。
一个午后。我在拆除老宅 无意间 让它重见天日。
拂去蒙封在它身上的,厚厚的尘土 暗红的漆渍 明显出现斑驳的迹痕
它像个哑巴了许多年的兄弟 仍然 默不作声
直到我唤醒它 还是发出闷闷的 声音
——父亲走后,这架算盘便开始接受了 人间的冷落。它与我 意外的相逢,仿佛是一对 失散多年的父子 意外的相逢
删除
删除天空上悬浮的黑云,和云层里暗藏的匕首 删除大地露出的骨头,和骨头之外的犬牙交错 删除无休止的战争、掠夺,和一纸协议下的暗箱操作 删除卑劣者、抢劫犯、道貌岸然的腐败分子 删除地震、洪涝、火山爆发,甚至删除人世间 所有的不屑之词。让正义的风暴,张开拉枯摧朽的大弓 让高高的庙宇,安放下弱小的肉身
寂静
在说寂静的时候,他们仿佛 是两个奄奄一息的人。仿佛是 两尊泥塑。或者是失去声带的两个人 一个在伺弄油腻的老烟袋 一个在老花镜下,不断翻剪修补 陈年累月留下的破旧衣服。他们 都不说话,似乎 一生中的语言,早已说尽。有时候 他们,只是摆摆手,点点头 相视一笑。有时候 他们只是指指偏西的日头,或者 指指院子里,喊叫的猪羊。他们 只是用肢体来完成表达。他们 喜欢这样的表达。但 更多时候,他们是寂静的。 从未打破。几十年了,他们 一直在寂静中度过,从未打破。那怕 一星半点的声音,都会打破他们 心有灵犀的时光
在唐山登凤凰山
九月十日,从丰润折道唐山。 在大钊公园乘游3路车,途径三五个站点 就到了凤凰山。
山脚下,车流如织 人间一派忙乱。
我顺着石级,曲径而上。 此刻,一座城市仍然安卧在万里江山。
忽然,想起四十年前,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场灾难 我的脚,竟然有些许的痛感。
凤凰山太高了 以至于挡住我回望北方的视线
大雾中
在雾中行走,车子擦亮眼睛。但是 距前方四五十米处 隐约有蹒跚的老人 负重的影子
荒郊野外,是什么原因 让他背负满腹的心事?又是什么境况 让一个老人,踽踽而行在 如织的车流中?
在打消疑虑的一瞬间,我看清 老人并没有走动,只是所有的车子 在走动。只是,在距离老人前方不远的路面上 有一个深深的凹陷
——大雾笼罩下,有时候 一些不确定的事物,反倒会 慢慢清晰起来
|
|







 好诗共赏!
好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