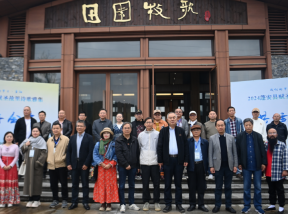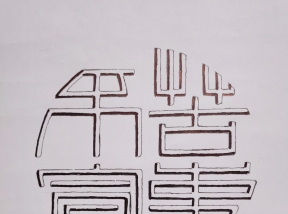|
焘硕|在故乡(组诗) 在故乡
在故乡。我把一座山
认做父亲
把一条河流认做母亲。他们敦厚善良
都是朴素的样子
在山上,我与草木称兄道弟
从父亲的身体里
取出五谷,取出陈年老酒。小心翼翼
供奉在山神庙前
我和山神都是吃五谷长大
因为心怀敬畏
我不敢与山神碰杯
敬畏山神就像敬畏父亲
在河边。我把野花认成姐妹
用母亲体内的水
洗濯爱情。每一朵鲜花都张开笑脸
用柴禾和炊烟
说出人间烟火
在故乡。一座山沉默寡言
一条河胸襟辽阔
他们相濡以沫。把血脉中优质的基因
都赐与我,让我像一座山
也像一条河
秋风起
秋风起时,把我头顶的天空
吹远了许多
抬头,天高云淡。蓝的更蓝
白的更白
没有谁比此刻的秋风更懂我的心情
它把一棵谷子
吹成我的模样,低垂的头颅
叩问大地
人生何其苦短,每一棵植物都替我
说出心中的悲悯
我没有镰刀的蓬勃之心
面对一场浩大的金色浪涛,充满兴奋
像秋风中的小草
内心老气横秋,外在渐渐枯黄
我与一棵谷子互相凝视
彼此更像故人
秋风吹过
我摇一下头,它晃一下身
把人间甘苦
相互倾诉了一次
草说
说到草,内心就有绿色葳蕤
有潮湿的水雾
从眼底升起
心底柔软的部分,像草一样起伏
一棵草有多么孤独和卑微
只有风知道
风吹草低,能听见草的骨节哗哗响动
她们不喊疼
仿佛风吹草动的日子,更适合
这些草民
把骨气交给东风或者西风
不是失节
用纤细柔软的根茎
攥紧一把泥土,把生命一次次绵延
每一个轮回
都要把人间的悲苦、冷暖和孤寂
重新品尝一遍
我和草都是本草一族
生在北方
把一棵草,认作草原
胸中的辽阔
能放得开马蹄,盛得下牛羊
能让一朵白云
来回地飘 冬日书
这个冬天,最大的手笔
就是千山飞雪
鹅毛般的狂草,把冰冷的偏旁和部首
写成故乡的姓氏
随我漂泊
雪下
我卑微的祖籍低到尘埃
把言正子这个村名,深深埋住
我思念和牵挂的亲人们
像一窝土豆,在窑洞里繁衍
亲情生生不息
炊烟是最美的人间烟火
雪一压就弯
灶堂里的柴禾替母亲喊出方言
交出内心的烟火和温度
把一壶酒烫成幸福的样子
雪花飘得高深莫测
西风的套路吹得太深,只一会就把
夕阳吹落
吹成一盏油灯
点亮我的归途 田野 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是谷子 根扎得越深 腰弯得越低。仿佛茫茫田野 使劲按住我的头颅 往土里摁 父亲就是这般,把一颗土豆 摁进地里的 摁进地里的土豆,终于开出白色的花朵 秋风吹的时候 地里就长出一窝大大小小的土豆 父亲每年如此辛劳。把五谷杂粮 和农历的节气 一起摁进地里。田野就长出丰衣足食 摁着摁着,父亲就老了 把自己也摁了进去 我才知道,这广袤的田野 生长万物 也生长我们的姓氏 老井台 在老井台,他用辘轳 把一桶夕阳 提上来。半桶水花晃荡,溅出 细碎的水珠,像泪 他把自己的脸 挪到桶前。桶里是一张苍老的面孔 在水里摇晃。一会儿模糊 一会儿清晰 三十多年了,他每天都在照 辘轳吱吜着 像一把锋利的刀,蘸着漫长的岁月 刻出沧桑和疼痛 他忘不了,那个在井台上 临水相照的女人 忘不了她坐上花轿时撩起的那道眼神 他每天把井里的水提上来 又倒回去。仿佛在打捞一个女人的心事 可桶里的水还是那么清澈 能照见他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