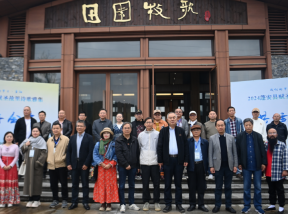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诗坛快递 于 2020-5-1 20:52 编辑
《1966年》 东方出版社
王小妮:吉林省长春市人,诗人、作家。1985年起居深圳。曾插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最新出版有旅行随笔集《看看这世界》,著有小说《人鸟低飞》《1966年》、随笔《上课记》《上课记2》《随手》、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等。
自我屏蔽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 作者:王小妮 来源:凤凰网文化 凤凰网文化:《1966年》被评为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又入围了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这么受欢迎,您之前想到了么?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王小妮:因为它写的是讳莫如深的1966年。 凤凰网文化:书中写了11个故事,全都是您的创造,还是其中有身边真实事件的呈现? 王小妮:有恍惚的真实的碎片,但它们是小说,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在写文革,早先的《方圆四十里》写知青,也是文革题材,很多和您同龄的作家、诗人都以文革为重要写作内容和思考内容。您觉得文革对于您人生和写作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王小妮:每个作家都有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想,好的作家身上应该有的不是趋同,而是差异。 《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都是虚构的叙事,其它文体不容易承载这段历史。如果有一本日记就珍贵了,当然前提是“真日记”,它的还原性应该更可靠,可惜,在那十年里,几亿人里,恐怕没几个人能留下一本“真日记”。没有记录只好虚构。当一张嘴说出来的,都不是心里所想的,这种情形延续多年,无数真切细微的感受都流失掉了。 短篇集《1966年》和长篇《方圆四十里》,都有特别留意“真切”和“细微”,更想向读者传达身在其中的感受。 1966年的人们恍惚和惶恐,到了《方圆四十里》写到的1975年,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分离人格和部分的看透,这变化是用时间用人性悟出来的,可见蒙昧不可能长久。 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一个狂热投入的少年的故事。最后和《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一起,成为文革三部曲。 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逐渐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 凤凰网文化:文革成了您的底色,该怎么理解?这种底色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 王小妮:恐惧和怀疑,对群体的天然防范,遇到信誓旦旦的事,不会听信,自己判断。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而且文字平和。这让人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自己觉得呢?这是不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一种特殊能力? 王小妮:对不起,没有读过《干校六记》。各种各样的作家,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风格,共性应该很难归类个性。 《1966年》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15年前了,最开始是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原准备每月写一篇,一年连载12篇,后来有点编刊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第12篇手写的提纲现在还在,没有动笔。 凤凰网文化:其实1966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如果不是现实这种写作环境、话语空间,比如可以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等等,《1966年》还会选择一种避开正面冲突的灵动的写法吗? 王小妮:永远没有被写尽的题材,1966更如此。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可能隔着一面墙壁一条胡同就有很惨烈的事情正发生着,当时非常清楚,我要写的仅限于这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也得看到,自我屏蔽的功能常会自动自觉地打开,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吧。 如果有更自由舒展的“写作环境”,我的切入角度也不会是直统统的,但是会更多的直面当时,努力恢复能感知到的所有,全息的,而不是有躲闪有回避。 凤凰网文化:自我屏蔽的功能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意识?恐惧、失语,还是什么? 王小妮:自我屏蔽的功能早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选择性发言,人人以“趋利避害”为先,最后形成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己”永远见不得台面,永远委身在高调又正确的集体之下,只为求得安全的存在,它渺小和隐蔽,却结结实实凝固成一个人的内心之核。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所谓的社会风气怎么能由坏变好? 写字是自救方式 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凤凰网文化:您的文字有种说法,“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刀伤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种不忍心,还是认为针刺的力道更大? 王小妮:没有不忍心。忍心承受,不忍心写出来? 虚构作品和非虚构相比,前者的优势是有选择性,它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我始终以为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凤凰网文化:虚构作品比非虚构更有选择性,也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那么您会尝试用非虚构来写文革吗? 王小妮:最有力的当然是非虚构,可惜没有可信赖的素材,可遇不可求。见过几本文革时候的私人日记,除了抄语录表忠心,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比如这一天干了重活,很疲倦,他不会写今天很累,他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个人要有意在日记里模糊掉真实的自己,这已经不是“非虚构”而是“虚构”了。也有人在日记里夹藏暗号暗语,可时间一久,忘了暗号的代指,成了一本失效的日记。 凤凰网文化:您是一个是诗人,开始写小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小妮:我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人,换一个文体不困难。和诗比,小说要耐力,也更舒缓更理性吧。 凤凰网文化:您是东北人,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语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体现出来的写作经验。我不知道在诗歌写作中,这种经验会不会有?毕竟诗歌比小说要更加抽象、想象力也更加发散。 王小妮:小说中的方言是有意的,特别在《方圆四十里》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写诗的时候,方言几乎没跳出来过,我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如果是,就不一样了。 凤凰网文化:小说为什么有意使用方言? 王小妮:为了还原。 凤凰网文化:您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那么这对于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小妮:东北方言应该不是个独立语系,其它方言可能影响思考,我感觉东北方言没有这个功能。 凤凰网文化:写作《1966年》和之前写《上课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哪个难度要大一些? 王小妮:没有遇到难度,只要遵循每部作品的独特性,自然会清晰顺畅。《1966年》要还原得恰如当年,《上课记》面对大量原始材料,在取舍定位和忠实记录上花费心思。 凤凰网文化:很多作家叙述自己写作过程时都会谈到各种各样极致的体验。我想知道,您的写作是不是总是一种愉快的自然的经历,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因为看您的文字总是平静、稳当的。但是在大学任教那几年有些除外,您常常感到失望和悲哀。 王小妮: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创造的快感。 不只是在大学任教的几年,只是《上课记》,特别是《上课记2》把这种心情透露出来了。失望和悲哀,几乎凝固成了人生底色,前面说过它始于那个年代。 凤凰网文化:您说两部《上课记》写的是心情,那您会怎么评价当下的教育? 王小妮:今天一早看见教育部说四个决不。建议把外语和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等和中国无关的课程一律取消,我们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了。 凤凰网文化:《上课记》出来以后,很多媒体都在找您谈教育,把您当成了一个教育专家。或者至少期待您能像陈丹青一样在离开教育体制以后转身开炮。 王小妮:两本《上课记》就是我的开炮方式。我和我的学生说过,不要做一个愤青。 当然不是教育专家。非要说专家,做个写出真感受的专家,那才好。 精神最匮乏的几年 人们逮住诗填补自己 凤凰网文化:外界把您的诗歌起点划进朦胧诗,您自己认可吗?您对自己的诗歌经历有一个怎样的分期和定位? 王小妮: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有些做评论的也太刻板太爱给人定位了。 我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 凤凰网文化:您说过“写诗不可努力”,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说诗人都是天生的? 王小妮:并不想特别强调天赋,更想说的是写诗不要太有“目的性”,写下来就是全部目的,然后是另一件事。 凤凰网文化:您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和那个诗歌年代怎么评价?与您前后成名的许多诗人,后来都抛弃了他们曾经的诗歌语言和思考方式,或者在诗歌形态上进行尝试,或者高度的形而上,或者追求史诗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些转变? 王小妮: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那时候,它通达到每个人的速度最快,传播障碍又最少。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写或者不写,这样写或者那样写。 凤凰网文化:“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对于诗歌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王小妮:诗本身只是个形式,没情感没选择。万幸的是还能写诗的人。 凤凰网文化:今后还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诗歌时代? 王小妮:也许有,诗歌时代出现的前提很可能伴随一个极不正常年代的出现或过去,从在个角度说,还是没有好。 不喜欢被关注 我和萧红不像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一直都远离群体,无论是知青身份,还是诗歌上的某种流派,好像都被大家忽略掉,因为您哪里也不怎么出现。 王小妮:我不喜欢被关注。 凤凰网文化:您很多年前写过《人鸟低飞》,是关于萧红的。今年正好有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被谈论的挺多--《黄金时代》,其中关于萧红的一句话被大家频繁提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猜想,当时您写萧红传记是不是就是被萧红这种性格吸引?是不是在这点上,您和萧红是相似的? 王小妮:《人鸟低飞》写在20年前,忽然萧红很红,是这几年的事情。关于她的电影我一部没看,演员是很难演作家的,或者说,一个人是很难演活另一个人。插一句题外话,如果未来有一天,1966年不敏感了,我要自己把《1966年》改成一部电影剧本。 当年写萧红,是喜欢她的作品,和我们相识的人都很难真了解,何况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人鸟低飞》是一部小说,不是严格的人物传记。 按我对萧红的理解,性格上应该很不像。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普希金在锅炉里 选自王小妮的《1966》,全书由11个故事组成,是全书的第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父亲说话了,他说:现在,你们都坐好,我们要开一个会。 四个孩子都是刚从室外被叫回来,由寒冷进入了温暖,他们的脸好看地发烧变红了。两个大点的孩子心里说:开会的意思,就是要讲一件坏消息。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本来,他们一家人都应当坐到吃饭的房子里,各有各的位置,那才更像开会。但是,从夏天以来,那间房子谁都不愿意多呆,太阳再也照不进那间朝南的房间。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纸上写满了字,带着墨汁的臭味,有时候来几个看热闹的,把纸上写的内容大声读一段。这一家人的餐厅变成了谁都不想停留,又躲避不掉的地方。 父亲说:天冷了,过去一到冬天,单位都会派过来一个锅炉工,给我们烧锅炉,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不应该,非常错误! 最大的那个男孩打断了父亲:这不怪我们,谁让这个锅炉只管我们一家的,这是以前建房子的日本鬼子的错。 父亲打断儿子说:你小点声,我们住在这,现在就是我们的错误,从明天起,你们四个也要学会劳动,劳动最光荣,反正都不上学了,老大负责早上钩火,火要是灭了,你负责点锅炉,老二负责添煤,三儿和四儿一起负责倒炉灰,从今天往后,万一家里大人不在,这个分工也不变,你们都要记住。 大人怎么能不在,哪个家里没有大人光有小孩呢,四个孩子想。 最大的男孩说话了,他有点不情愿:去年来的那个叔叔,天还没亮就把暖气片烧得很烫,点锅炉得几点钟起床呵? 母亲第一次说话,她说:妈妈和你一起来,早上我帮你。 最大的女孩说:爸爸从来不让我们进锅炉房,我不懂在什么时候该添煤,我怕把火给压灭了。 父亲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认真,没有学不会的事情,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他才说了这么短的一段话,就引用了两条语录本上的话,懂喊爸爸妈妈的小孩都知道,那话不容反驳。 太阳在这一天提前降落了。窗户上结了薄霜,凝血那样的暗玫瑰色。因为还没开始烧锅炉,一家人都感到哆嗦,不只是皮肉,骨头节儿都在哆嗦。父亲站起来说:早点上床吧,进了被窝就不冷了,我给你们烧热水鳖去。 父亲把开水壶的壶嘴儿对准了白陶瓷的水鳖的嘴儿,它的形状的确像一只硬壳的鳖,有点憨笨,装了热水它很快变烫了。 父亲听到流水声,在他能控制的均匀的流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声响?他试着辨别流水以外的响声。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又马上从自己家的某个角落里挺身起来,他要喊得响亮一点,他说:到!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紧张短促,像一段折子戏,已经在父亲的脑子里彩排了无数次,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他都感到了不耐烦。 热水鳖窜热了四个孩子的被窝。现在它卧在父亲穿着棉衣的怀里,他的胸腹前面格外诚实而温暖。母亲在掀平一张绿色细花瓣的棉被,她说:你不睡吗?父亲低声说:我听见起码有三个人从窗户下面过去,就紧贴着我们家的墙。父亲和母亲忽然静止,同时停止了一切动作。 烧锅炉这种事情,这一家人谁也没做过。天还没有亮,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大男孩一起在小锅炉那儿忙,木头劈柴燃着了火,发出树木的香味,煤被劈柴点燃发出臭味,也许木头喜欢燃烧,煤厌恶燃烧。屋子里很快注满了烟,三个人都在擦眼泪。父亲说:有烟最好了,有烟说明煤还没灭,有烟就有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敲门声,透过狭长黑暗的走廊深深地传进来。父亲垂下两只抓煤的手,他停了一下,才说:都别动,别慌张,我去开门。 在乳白色烟雾的锅炉房里,父亲看见妻子和儿子的脸跟两只瓷挂盘那样定在空中。敲门声并不很急促,有点虚弱。父亲想,这几乎就是我在敲门呢,除了我这种岌岌可危的家伙,还有谁这么胆小? 父亲用了点力气,打开结霜的门,外面站着个穿棉大衣的高个子,嘴唇里正吐出一串长椭圆形的白气。等气散了,很年轻的脸才露出来。你找谁?父亲问。 年轻人放下狗耳朵一样立着的大衣领子:我去年给你们烧过锅炉的,不认识了吗? 他们就站在门口的一个下深的台阶前说话。这是一栋日本人战败撤离后留下来的老房子,他们站的那角落,在日本语里叫玄关。 年轻人说:今天是给暖气的第一天,去年就是今天,我来你们家烧锅炉的,我日记上都记着呢,今天我又来了,还带了引火的松树明子。 父亲感到很为难,他的嘴唇里不断地说:可是,可是……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脑袋里像注进了混凝土。终于,他尽量委婉地说话了:可是,烧锅炉,这是单位里才能决定的事情,再说,我们已经想好了,自力更生,这个小锅炉,今年我们自己烧,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话吧? 年轻人把两只手从很窄的大衣袖管里抽出来,这之前它们一直抄在袖子里。他说:再不一样,冬天也是得冷,锅炉也是得烧,对吧。 父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问:是我们单位叫你来的吗? 说完这话,父亲感到身上的毛孔都立起来了,他像一只受到了突然袭击的刺猬,带着浑身的刺,他想:现在,可不敢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 年轻人又吃力地把手袖起来。他说:是我自己来的,我没报考大学,在家里也是闲着,想找个事做。 父亲打断了年轻人:可是,烧锅炉得请示组织。组织上不让,你就不能来,同志!你和我,谁能不听组织的? 这时候,大男孩从长廊另一侧跑出来喊:爸,灭了! 这个孩子带过来的煤烟味一直顶到了大门口。 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不是要跟你们单位领一个月十五块的锅炉工钱,我就帮你烧几天,我连单位也没有,一个社会上的大闲人,等你们自己能烧了,我就不来了。 男孩子和他的母亲,还有刚爬起来的三个女孩都站在玄关后面的台阶上,把屋子里暗黄的灯光几乎全挡住了,使两个说话的男人站在暗处。 母亲说:上班快晚了,我还要去开会。 父亲听到开会,开始移动身体,他抬起脸,看见最小的女孩穿着已经变短了的棉猴儿,短头发睡得全部翘起来,瘦弱哦,像根满脑瓜挑着毛刺的蒲公英站在那儿。父亲说:这样吧,你 教教我孩子,让他们一个礼拜以后就能自力更生,一个礼拜,以后再不麻烦你,就不劳驾你来了。 在马路上,父亲和母亲分别推着自行车走。在路口分手的时候,父亲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然后,他又说:那个非要来给我们烧锅炉的,不是谁派来监视我的吧? 母亲说:看着不像,去年他住过来那几个月,除了烧锅炉,就躲在他的床铺上看书。 母亲伸出手,在丈夫的自行车座垫上推了一下,父亲感到了一股力,他的自行车自觉自愿地向前滑行,两个人就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开始飘雪花。天还没彻底亮起来,还保持着深蓝墨水的颜色。雪线是斜的,一直向着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奔走,像很尖的狼毫笔在黑纸上勾出无数白线。父亲被这场雪下得满心烦乱,开会这个词,在他心里是一个多可怕的漫天旋转的怪物哦。现在,他又要去开会了。 雪从此没停,稀稀拉拉一直下了四天。 晚上,父亲在雪里回家。自行车的前轮把雪轧得吱吱叫,雪的叫声是最可怜短促的哀叫。父亲尽量把自行车骑得慢一点,他准备在路上把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都理清,让自己回到家以后,什么都不再想。可是,他哪里左右得了意识?已经看见家的灯光,脑子里还是污浊混乱的一团。 父亲用戴手套的手,轻微地敲门,里面一片咕咚咕咚的孩子们的脚步响。那些让他时刻在惊恐中等待着的人,未来一定也是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敲门,和他现在所用的力气不同就是了。他听到孩子们都在门口等他了。 父亲的眼镜片在进门以后立刻蒙上了白霜,他把眼镜拿在手里暖着。由于近视,他看见的不知道是几个孩子了,晃晃地很多哦,甚至还闻到了婴儿身上的奶的气味。在这么冷的冬夜里,又能回到家,见到家人,这使他很感动。他坐下来,脱掉棉鞋和毛袜子。四个孩子抢走了它们,每人拿到了一件。鞋袜都贴在温暖的暖气片上,它们每到冬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居然在这一年也没变。 最小的孩子说:爸爸,那个叔叔把锅炉里面都烧红了,我看见了! 父亲问:叔叔呢? 孩子们一起说:走了。 1966年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晚上,没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真安静的晚上。 傍晚时候,女孩戴了一顶红毛线的帽子。她站在家门口,看着街上的孩子们在滚雪球。雪并不厚,雪球不可能滚得很大。街上散布了一些被抛掉的老白菜叶,冻成一条条透明的死鱼形状。有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这雪站不住!说话的人在街对面一棵很秃的唐槭树下面站着,是个老太太,围一条毛毡似的织物在脖子上,她的袖子上别着一块红布,不知道她站在那儿,是要管什么的。女孩想,雪是怎么站住的?雪又不是一个小孩儿,又不是一只酱油瓶。她还不明白,雪站不住的意思,是雪会融化掉,肮脏的马路会再露出来。而女孩希望每天都下雪,每一场雪都能站住,这样到处都是白的,这是一个被白雪公主之类童话给蒙骗的孩子。 女孩从来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她习惯了,因为她从来不跟其他孩子玩,因为她母亲说:满街疯跑的都是些野孩子。她早习惯了远远地看着别人玩。在她的家门口看不见有轨电车,这中间隔着一些不高的俄式建筑,隔着些洋葱头,电车叮叮当当地在另外一条马路上驶过,它一定正在拐弯呢,头顶上冒着绿火星。 女孩看见一个人,那人正从树和雪之间走过来,没有戴棉帽子,所以,头顶是白花花的一层雪,他背了一个蓝布书包,好像很沉重。她认出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他又来了。为什么过去她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人? 来到木栅栏围住的院子门口,年轻人伸出两只手,快速抖落头上的雪。他的一只肩膀耸起来,一只手伸进木板门的缝里,灵巧地拨开门闩,动作很熟练。站在院子里的女孩一直盯着这个很少讲话的年轻人,这个来烧锅炉的,她的心里涌现出一种随着雪片倾斜着飘舞的感觉。 后来,天慢慢变得更昏暗,下班的人骑着车,纷纷在街口拐弯的地方摔倒。有人故意在那个必经之路泼了水,水很快结冰,新雪又盖住了冰,谁骑到那儿都可能摔。几个男孩躲在墙角大笑。女孩觉得她并不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她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暖和又有好看的颜色。下雪的晚上,地面反而比天空还亮,它也顺便给这个安静女孩的心里洒了一层稀薄的光。 女孩的母亲在切土豆丝。过去这是保姆的工作,那个南方口音极重的保姆走了几个月了。母亲一下班就在厨房里乱转,经常自言自语:盘子,盘子,盘子都在哪儿? 现在,女孩摘下红毛线帽子,听见母亲正和烧锅炉的年轻人讲话。她说:这么晚了,你还跑来,真是麻烦你了。年轻人说:顺便来看看,没想到两个小学生也能烧锅炉了。 母亲说:饭好了,吃了饭再走吧。 女孩想,他能留下来吃饭吗? 桌子上是一盘标准面粉蒸的馒头,每人一碟土豆丝。年轻人客气了一下,最后很轻很轻地坐下来。刚才,女孩从厨房的门缝里看见,他一直在水池前用肥皂洗手,他的手指头像刚剥过皮的水萝卜一样又细又长,水亮亮的。年轻人很拘谨地坐着,正好在女孩的对面,只要抬起头,女孩就能看见他狭长的脸,而且他还有胡子,脸的两侧都有哦。女孩还是第一次注意到父亲以外的男人,原来,他们的脸上都会有胡子。 玻璃窗上结满了霜的花朵,这间房子在夜晚变得古朴和温暖。今夜的霜花像许多条孔雀的长翎翻卷着,冬天的白孔雀把窗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挡住了,深蓝的晚上是孔雀翎的晚上。但是,女孩的父亲沉着头不说话,桌上只有吃饭的声响。女孩非常小心,她吃得尽量轻而且慢。塑料台布上那些暗绿色的小格子,是女孩一直都喜欢的图案。她把两只手并排按在几排格子上,感觉这个姿势很优美。 父亲抬起脸来:他问:小二,你吃完了吧? 女孩马上收回手,她悄悄地离开了桌子。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吃完了。 父亲和母亲住的房间地板上堆满了书,很久以前就捆好了。女孩早侦察过的,有几捆书都是孩子们的。她摸着黑,用力抽出其中一本,赶紧溜回到自己的床上。 瓷碗和瓷碗相撞的声音。女孩听到父亲在玄关那儿说:以后就不麻烦你了,他们能烧好这个炉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几岁的孩子早该锻炼锻炼了。 年轻人说:我还是抽空来看看吧,也许白天来,也许晚点,反正我也是个纯粹的闲人。 父亲又说:去年冬天,让你住那间洗澡房里实在太不好了,对不住了,工人阶级有充足的理由住得好一点,过去思想有问题,做的错事太多。 年轻人说:没什么,我住哪儿都一样,都很好。 后来,通向外面的门很沉重地关上。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穿上他的棉大衣走了,踏着雪。霜花太厚,使女孩不能通过玻璃看见他。她身上出现那种刚喝下一大杯甜葡萄酒之后晕晕的感觉。 在走廊里,父亲问母亲:这小伙子家里是做什么的? 母亲说:刚才问过了,他父亲是教书的。 父亲说:教书的?教书的怕一个也躲不掉。 女孩听见父亲走近,马上把刚偷的童话书塞在被子下面。父亲的黑影落在房子中间。他手里托着热水鳖,侧着脸,一动不动地听。女孩觉得父亲在这一年里变得很怪。 下雪的天,分不清上午和下午,天反正是昏的。女孩看一眼钟,是下午两点钟,这种时候家里最安静,其他的孩子都在午睡。 女孩来到洗澡房,那扇房门松垮垮的,快掉下来了。整间房子比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木架子上面铺了几条木板。去年,为免得早起,免得赶很远的路过来,烧锅炉的年轻人在这儿睡过一个冬天。到了夏天,保姆在这儿摆放大笼屉,几年前,母亲还在这儿藏过盛白糖的铁盒子。 现在躺在木板上的是她了。女孩的身体很小很轻,她身下木板的吱吱声也微弱。天花板上有墙皮剥落以后留下的图案,女巫的鹰钩鼻子顶着一只硕大的灰桃子。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 每天也是对着这个女巫和桃子睡觉的吗,也像她现在这样平平地躺着望着天? 就是这时候,女孩发现木板最里侧放着一个蓝色书包,很鼓,前一个晚上,年轻人来的时候背的正是它。书包旁边有一个硬皮的本子。对于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最神秘的就是藏在角落里的这个书包和本子。女孩看见本子的封面有一行竖写的金色小字:江山如此多娇。她知道,这是关于雪的一篇诗词,金字当然是伟大领袖的笔迹,除了伟大领袖,没有人能写出金色的字。女孩打开那本子,看见了下面这些字:
啊!这就是我曾爱过的人, 我火热的心曾为她那么紧张。 你的气息有怎么样的火焰, 殷殷的目光怀着多少情意。 在琥珀珠链下, 你洁白的胸流着红色, 在微微地颤动。 昨晚上,她竟如此微妙从铺台布的桌子下面, 向我伸来小小的脚。 我过得孤独而忧郁, 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
天啊,这是写的什么,女孩好害怕,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些中国汉字组合在一起,还是纯蓝墨水写的,整整齐齐的。这是烧锅炉的在对什么人说话吗? 女孩看过的唯一一本父亲的书是《红岩》,她没再看过任何别的大人们的书。可是这烧锅炉的是个怪人,这些可怕的字把她吓坏了。合上有金字的本子,手指头还在发抖。女孩飞快地爬下光秃秃的木板床,一边跑一边听着心跳。拉着她自己的棉被,缩紧着躺下,又拉棉衣盖住脸。可是,有一团东西继续追过来,她不停地想遮挡,不停地躲。她想: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字呢?这一定就是被抓住捆起来满街游斗的流氓吧,就是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头认罪的人吧,一定是的,是最坏的坏蛋。可是,那些水汪汪的蓝色字迹,总跑到她眼前来闪烁跳跃,好害怕的词哦。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跑到门口去说:姐姐病了,整个下午,她都不起床,蒙着头睡觉。 母亲的手上还带着雪腥味,她去摸女孩的额头。母亲说:不热,没有发烧,是头疼吗。 女孩的眼泪忽然向这世界的左边和右边簌簌地流出去了。 这个晚上,雪依旧时停时下,女孩家的楼上发生了大事情,把他们全家人都惊醒了。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上面住的另外一户人家,楼板上不停地有很重的东西翻倒。有很多的人喊,很多的人穿很重的皮鞋跺脚,铁钉刺刺地划地板。父亲站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他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不要哭喊,我们没有做一丁点儿的坏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最大的男孩说:爸,睡不着。 父亲说:塞两棉花团,往耳朵里塞,很快就能睡着。 过了很久,楼上才平静。下雪的夜里,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都会是格外平静的。 女孩光着脚走过地板,摸到父母亲的房门口,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在犹豫。父亲的声音传过来:是谁起来了,不是告诉你们塞棉花团了吗。 女孩站在一团漆黑里,她说:爸,我做了坏事儿,我看见了一些很不好的话。 两个大人很快起来,拉亮了灯。 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吗,那个小子,装得真够老实的,把什么普希金什么莱蒙托夫这么一堆东西都弄到我们家来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父亲把有金字的硬皮本子打开又合上,反反复复,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要动手给它个耳光。 两个大人把书包里的书和硬皮本子都抱到锅炉房,书都倒进盛煤的木箱里。父亲说:真不明白,害人还要怎么害呢,真是不明白,我们无冤无仇啊。 锅炉的小铁门上铸着几个日本假名,父亲打开炉门,把硬皮本子在锅炉角上重重磕了一下,塞进炉口去,没有看到火苗,也没有烟。父亲又把书一本一本地卷成筒状,都塞进炉子。他说:本来咱都就够受了,明天,他再来,不让他进门,赶他走。 炉膛里面的火被煤压着,书本暂时没有燃烧,平展展地摆在里面,它们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父亲起身四处找火柴,什么地方都去摸几下。大人的慌张,让女孩更害怕,站在锅炉房门口,她想自己一定是做错了,那个本子应该是他的东西,没经过他同意,就这样被父亲给塞进了锅炉,那些字就要起火苗了,这么做对的吗,那个年轻的锅炉工不会伤心吗? 父亲当然拿到了火,他划,火在他两只手里捧着,他喊女孩过来用铁钩挑开炉门。最后,他接过炉钩翻动瞬间变成灰的那些纸。这时候,母亲慌慌张张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她说,这书我们家也有一本。父亲说:我也买过普希金,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家也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还是一模一样的。这回,是自己的书,燃烧速度比刚才快了很多,炉火已经燃起来了,这本书刚进炉膛,只有很短的一小会儿,它坚持保留着一本书的现状。 很久很久,两个大人都没留意锅炉旁的女孩,好像她根本不存在,好像她是这锅炉房里自然升温的热空气。她太小了,除了小,她什么也不是,虽然幸好在这个平静的晚上,她发现了暗藏的危险,通知了大人,让他们做了避免危难发生的补救。 终于,母亲回头看见了她。母亲说:快上床睡觉去,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还光着脚,快上床去。 什么是普丝巾?她问。 父亲推她的背,推着她走向走廊说:一个写字的坏人,还有锅炉工,他把普希金抄在本子,他也是坏人,和普希金一样坏。 女孩一直走向她的床,捂住两只冰凉的脚,怎么都睡不着。她感觉对不住那个人,她把他出卖了,可是,如果是一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写那些恶心的字,如果真有一个又恶心又坏的,那应该是普丝巾,不该是烧锅炉的人。 雪并不准备停。偶尔一盏还没被打破的路灯面前,必然扑动一团晶亮又过度活跃的雪花。突然这样的路灯也灭了,因为,天就要亮了。烟囱里吐出来的烟都不愿意离开街面,它们压着大地走,冬天里的北方人又醒过来了。 年轻的锅炉工走得不快,一辆热气腾腾的豆腐车急急慌慌慌赶路,推车的人戴着肮脏的口罩,只罩住了嘴,两颗大鼻孔黑乎乎地卡在口罩上面。早起的人们紧追着豆腐车,喊着:别走了,你就在这给我们捡块豆腐吧。他们紧围住豆腐车,人人手里举着准备装豆腐的盆,铝的,搪瓷的,磕碰起来,响声不同。年轻的锅炉工绕过热气腾起的豆腐车,在他的喉咙里念诵着俄语: 我过得孤独而忧郁, 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 这是一个人内心里不出声的早祷。现在,他在想那张夹在硬皮笔记本里的棕黄色的照片,它在今天就会到达一个最平安的地方,一定要在今天之内把它送走。那张照片上的苏联姑娘有两条粗得惊人的辫子,像两大捆垂下来的亚麻绳子。每次看到她的照片,年轻人都会想:中国有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她就是苏联的土地姑娘,生着那么茁实的粗麻头发。土地姑娘的照片是年轻人读初中时候得到的,为了强化俄语学习,这座北方城市中学和一所苏联中学结为友谊学校,班上每一个学生都被安排指定和找一个通信对象,苏联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烧锅炉的年轻人有了这个苏联土地姑娘的照片和她的五封来信。后来,双方没有再联系,信和照片一直保存在他的硬皮笔记本里。 他已经习惯了没幻想的生活了,既然家庭出身不许他报考大学,他就做一个临时给人烧烧锅炉的零工。他喜欢一个人守着锅炉,把微微喷湿的煤面儿抛散开再添进去,然后,坐下等待,听着风把炉子里的煤变成红炭,它的铁嘴里呜呜地抽出燃烧声,在这时候,读一本屠格涅夫,或者莱蒙托夫,或者普希金,世界就很美好。但是,这个冬天不一样了,这个冬天,跟哪个冬天都不一样。 年轻的锅炉工已经看见那户人家的两层小楼房了。去年,每次离开,他都习惯在这个街口停下几秒钟,抬头看看他的劳动成果,那房子的烟囱扑扑地吐些灰白的烟卷。这个早晨,他走得很快,开始敲门了。 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了! 年轻的锅炉工看见这家的男人愤怒的脸。 这句话,那四个孩子的父亲又重复了一次: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我把它烧了,还有你的书,你的本子,都烧了。外面再冷,我也不希望你进来,走吧你,我们家永远都不欢迎你。 那个母亲站在背后挑着棉门帘,她说:我们很害怕,你能明白吧,你的东西你拿走吧。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足够低声的,又低沉又短促。 锅炉工的手冻僵了,他去接他的空书包。那户人家的门很快关上了,没有等到年轻人离开。两个守着门的大人背后有一团黄色的灯光,本来是人的晃动,从外面看着好像是光在晃。然后,门就关了。 浑身寒气的年轻人,快步走向另一条街,僵硬的手在口袋里搜索到几枚硬币,正好有轨电车来了,早上的车空空荡荡,他跳上了车,像春天刚脱了棉衣服一样轻盈如飞哦。空的电车格外震荡,转弯时候,把人从坐席这边抛到坐席那边,两排吊起来的扶手都在头上欢蹦乱跳。年轻的锅炉工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想到了某部电影里的镜头,老人在黑夜里敲着梆子,拉着长声吆喝:平安无事啰! 全都没了,一把火,就真的平安无事了。 透过司机前方那块擦掉了霜的玻璃,正前方正冲过一辆广播车,它强行抢在电车前面冲过电车轨道。广播车顶的四个角都安装着大喇叭,四个方向都飘着红绸的旗帜。 年轻的锅炉工下车的时候,雪忽然停住了,背后的有轨电车正吃力地上一个坡路。天空好像干净了,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它的工作完成了。 一把火就换来了风平浪静,这把火竟然都不用他动手去点,他冻僵的脸有点笑了,吐向远方的长气,白的,冲出去,跑得远极了。过去的几个月,那个书包给他带来的危险比定时炸弹还大,比几辈子的财主的变天账还心惊胆战,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掉它。 年轻锅炉工住的是苏式大杂搂,房间是水泥地面,厨房在走廊尽头,是公用的,厕所是露天的,大杂楼附近是过去的满铁管辖区,现在住着很多铁路工人,警惕性极高,到处是长了凸冒眼睛的,他不可能当众点一把火,无论他烧点什么,都能引起怀疑,都是引火烧身。一个书包折磨着这年轻人,最后他想到去年烧锅炉的那户人家。他的屠格洛夫,莱蒙托夫,还有夹在笔记本里面苏联的土地姑娘,他抄的普希金哦,那个小日本造的锅炉应该能安全地销毁它们。那个铁家伙不会听声,眨眼睛,告密,喊话,它一张嘴,它们和他就都平安无事了。所以,天一冷他就想去烧锅炉,那儿是一块他能知道的最安全的墓地。 有点遗憾,年轻的锅炉工没能亲自给它们送行,看见那家人的慌张害怕,他明白他很安全。管它谁动的手,谁的手不是手,哪根火柴划着了不是火苗。那四角铸着铁花瓣的可爱的小锅炉。 这一家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连最小的孩子也会打开炉门添煤了。 女孩在饭桌上问她母亲:那个烧锅炉的叔叔不来了吗? 父亲和母亲一起说: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这一年的大人们必须用全部时间想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没挨饿受冻,他们根本顾不上孩子们。就像在一只铁锅里炒花生仁儿,他们把自己的前半生翻来复去地在灼热里滚,看着它们变黑变苦,变成焦炭。 终于有一个晚上,有人敲门了,也不是很凶猛。一些人冲进来,他们翻走了一些日用品,甚至搬走了旧式梳妆台。 他们的头目说:你们家里这么“干净”,一定事先都处理掉了。 父亲说:处理什么呢,本来就没什么,本来什么都没有。 他们走到锅炉房,马上说:看这小鬼子留下的锅炉,就是藏一把枪,这炉子也能把它烧化了,老实交待吧,都烧了什么! 父亲说:烧什么,烧的是最差的煤面子,今冬连成块的煤都不供应。 那些人都爬上卡车走了。 后来,女孩一直想在人群里再碰见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可是他彻底消失了。她没有任何根据地想象,那些诗,也许就是他写给她的。他给她写了诗,之后就很不好意思,就躲起来不敢见人了。 就是这么回事,好像一个童话,一个小女孩以为她在1966那一年遇上了一个写诗的王子。后来他无缘无故消失了,好像和一个叫普丝巾的有关系,谁知道后面的这个又是谁呢。 1966年的这个家庭,男人38岁,女人36岁。他们的男孩子14岁,女孩12岁,另外两个10岁和8岁。烧锅炉的年轻人21岁。
|